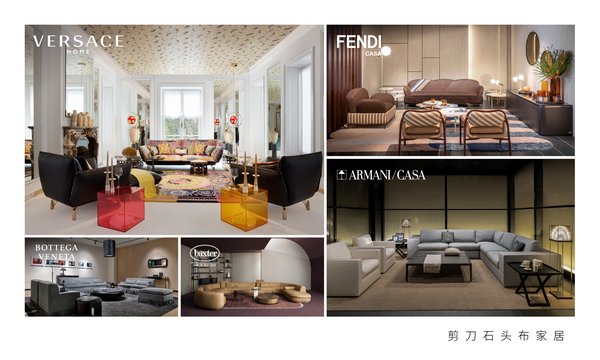杜冬
时间如大雪纷纷落下。
在318国道上一路西去,翻越二郎山,我又进入四川省甘孜州境内。
上次告别理塘时,罗桑喇嘛突然说:“你是被烦恼带来理塘,又要被烦恼带去上海了,你是烦恼的仆人了。”他的老师,一个更高更胖的格西,突然走过来,轻盈地在我脚背上踩了一下,然后仰天大笑着离去,就像一只硕大的天鹅。我没办法参透这禅机是什么意思。
藏族的谚语说,爬过长坡短坡,毫不停歇如手绕线团;翻过山梁山坳,如同纽扣一个接一个。
新都桥,高尔寺山,4600米,20公里的漫长河谷,八角楼乡,雅江城,剪子弯山,无数弯道,每个弯我都走了好多遍,放牧白云的牧人,西俄洛,卡子拉山,道班,红龙乡的喇嘛庙,大河边,终于到了我的第二故乡:理塘的山口。
在四周的山顶,时光厚厚累积沉睡在积雪中,如洁白的大块酥油,似乎是在准备一场天地间的豪华的法事。牧人驼背跨在瑟瑟发抖的马背,裹的如同一团牛绒。院场里晒的绛红色僧袍,已经冻硬,木板一样微微摆动。
这像是个漫长的午睡,鼾声连天,醒不过来。
然而理塘不同,理塘完全不同。
街头上,时间则如姑娘的发丝,一丝一缕地垂下来,像汗水闪闪发亮地流淌,羊毛从厚厚的藏袍下探出头来,试着风头。
摩托车上熟悉的音乐一掠而过,喇嘛的车把上假花摇曳,油箱般的音箱架在后座上。牛奶般的阳光里,宽脸的汉子迈着八字步,一只手上总是提着念珠,他的高大的面孔黝黑的女人,围着邦典和口罩,黑黑的大手蒲扇一样撑在邦典上。
午后依然漫长,藏居厚实的围墙反射着日光,日光从石头墙壁上酥油般淌下来,或者钻进石头缝里,将缝隙撑开。你可以把阳光和时间挥霍,送人,把阳光截成小条,再一一吹散,或把时间揉成一团,抛在脚边。甚至坐在寺庙的大台阶下,晒着太阳,兄弟一样搂着你的时间,将无处不在的空灵明净,想像成佛祖的模样。
无所不在的光明澄澈之中,一切有情众生等待着藏历年的到来。
今天一定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因为我起来的时候,曲西已经换好了鹅黄色的藏装,头发也扎起发髻,油亮的马尾辫垂着。措姆嫂子也换上新的邦典——措姆嫂子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也是全家最忙的,有时候快半夜了还睡眼惺忪地等着,给熬夜的我们倒茶水。此刻她的丈夫次仁还躺在一大堆乱糟糟的衣服里睡觉。
过年,一定要换上新衣服。拉姆阿妈以一贯的坚决,大声呵斥着,一把提起四处乱爬的孙子们,套上领袖口毛绒绒的新藏袍。孩子号啕大哭,用藏语抱怨着什么。我现在才明白今天要去理塘寺转庙,磕头拜佛,给长明的酥油灯加油。
阿妈拉姆笑着说:“娃娃不听话咯,我他们打了,再他们哭了。”
一条洁净的小路,沿着嘉木样活佛的故居和帕巴拉活佛的故居,直指理塘寺庙的大门。平时这里只有抬水的女人,今天则多了不少跪拜的朝佛者。出门的时候,爸爸泽仁在最后面,小心翼翼提着一只装满热酥油的铜壶,准备给佛前的长明灯续油。
阿妈拉姆在最前面,她不知道为什么生了大儿子次仁的气,脸气得发红,提起邦典围裙,用劲蹬着地面,攥紧拳头走在最前面。次仁披着衣服,嬉皮笑脸地凑过去,被她一把推开,或者说简直是擂开的。
我拍拍次仁的肩膀:阿妈凶的很哦。
次仁咧开大嘴笑,露出金牙:阿妈不凶的话,娃娃不听话。
寺庙的大门是玛尼堆和白塔,这是全康区最大的寺庙之一,俯瞰全理塘城,草原和318国道,左边是天葬场,右边是几个遥远的山间隐修院,寺庙和民居互相包容,合为一体,足足占了半个理塘城。
出发时,全家连孩子是十口,路上亲戚朋友们不断加入,到寺庙门口时,已经有了二十多人,横跨四代,典型的藏式大家庭,女人是最热心的信徒,拖着孩子,满心想着寺庙和磕头。男人走在后面,交换鼻烟。
高大的白塔肯定重新粉刷过了,亮的耀眼,好像悬空浮在寺庙门前的玛尼堆边。阿妈拉姆走在最前面,率先在白塔下磕头,她油亮的头发和紫红的手摩擦着洁净的白塔,从背上放下的孩子,揉揉惺忪的睡眼,也规规矩矩并拢双脚,把小脑袋碰在白塔下。
从白塔下的佛院,到正殿,到九廓,到法相院,最后绕寺庙一周。昏暗的佛堂里大小转经筒有如丛林,无数人从容不迫地转经祈福,阿妈们将白发苍苍的脑袋幸福地拱在柱子上摩挲。无数的亲戚,提着供佛的酥油壶,热情地问好,更多不认识的人,念着各自孤独的祈祷文。
寺庙边是理塘最古老的民居车马村,七世达赖喇嘛的故居仁康古屋就在此,仓央嘉错写了那首著名的“洁白的仙鹤”,所以他著名的失踪之后,人们认为他早已在诗歌里表明,他的转世会来到理塘,于是就在这座古屋里,发现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
这里简直是转经筒、木柱和佛像、经卷的迷宫,理塘寺里面阔大如堡垒,百转千折,阳光也被扭曲,浸泡,贮藏。有一次我们突然低头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头顶是数米高的佛经柜,刚刚出头,重重的佛经卷就突然砸到脑袋上,我眼冒金星。
眼前一个黑瘦的老僧人抱着一卷沉重的,丝帛包裹的经书,丝帛已经陈旧抽丝了:这是纯金的经书啊,他骄傲地说。这是黄金佛书在头顶的加持。这一记突如其来的黄金加持让我脑袋嗡嗡乱响,额头隐痛。
下午,家里热气腾腾地准备过年。阿爸泽仁在佛前供上日月形的面团,然后规规矩矩趴在床上磕了和自己岁数一样的头,他实在高大,磕头的时候地动山摇,几乎从床上摔下来。他也要让我磕,热心地要监督我。我看着全家期待的目光,只好说现在有点高反,脑壳痛了,晚上一定磕。
阿妈拉姆还气壮山河地指挥家里和亲戚中所有的女人,大约有一二十个,在阔大的厨房里不停地包拳头大的牦牛肉包子,半寸厚的包子皮加三两牦牛肉一个。整个藏历年期间,主食就是这油乎乎的牦牛肉包子“扑日”,女人们每天不停地包,不停地蒸,拿出全副力气,连续转移各家厨房作战。十家人家,大概总是要包一千多只大包子的。
女人们没完没了地捏包子。让男人看了胆寒:这么多包子都是要吃下肚的!
这简直是一场战役,热气腾腾,所有的藏桌上摆满了足够100人大吃大喝的饮料和牦牛肉,牦牛脑壳肉,辣牦牛肉,牛肚,藏猪皮,油炸的酥油果子“拉多”,这个时候才发现,理塘人家满面墙的大黄铜瓮并不完全只是装饰。
捏“扑日”肉包子是一场战斗,捏“拉多”酥油果子则是一场舞蹈。
将面粉和酥油用手调和,擀成直径一米的巨大薄饼,在上面均匀涂抹鲜红色的汁液,似乎供神的“朵玛”所用的红色,也是同样的染料。很快,一轮血红的明月就浮现在阿姨次松的手下。
叠层,切片,许多带着金戒指的手不停地捏制“拉多”,成型的拉多如同粉红的莲花或者手指,成群排列,被放入沸腾的油锅。阿姨次松和嫂子措姆交换着油腻腻的长筷,让拉多在油锅里尽情翻滚。
男子们也挤进来,坐在火炉旁边掏出手机来玩,声此起彼伏。他们对拉多没有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温暖,他们一定早已挤了出去。女人没有,甚至手机也没有,她们的手指上戴着崭新的金戒指,低垂双眼,看着油锅里的拉多。
灶台上还有个矿泉水瓶被人抛在一边,里面的青稞粒早已液化和粘稠,这可能是曲西家中某个男人突发奇想酿造青稞酒的随意实验,很有可能是阿爸次仁。成功的虫草商人阿爸次仁经过夏天的忙碌之后,整个冬季都极为清闲,他将大量的时间奉献给打牌。很显然,实验失败了,不知是不了解青稞酒的酿酒工艺,还是根本就忘记了。我不知道明年阿爸次仁是否还有勇气尝试。
阿爸泽仁提着小香炉满意地看着客厅里陈设完毕的各色饮料和食品,这是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最得意的时刻。
“我们这里哦,洛萨(新年)的话,钱多多地花了。”泽仁说。在理塘藏人看来,过年是各家各户显示家庭富裕和地位的重要机会,藏式新年是大家庭一起度过的,敞开大门,欢迎客人,所以全家人一定要显得体面阔气。
我和曲西还有她的哥哥姐妹们,半夜挤着去寺庙里看跳金刚舞,阿妈拉姆像对她的两个儿子一样,给我也穿上了家里昂贵的羊毛藏袍。寺庙里早就挤满了人,睡着了也不要紧,四周都是人,倒在其他人身上就好。无数人在深夜里呼出白雾,像是一堵云墙。
维持秩序的喇嘛戴着骷髅面具,挥着鞭子要大家坐下来,半夜里空洞的骷髅眼窝盯着你看,格外有新年的气息。还有流浪狗在人群中穿梭,本来,理塘的昼夜分明,白天是人的城市,夜里则属于流浪狗,但是洛萨就要来了,一切都不同。
寺庙大殿的门如今成了午夜歌剧的出入口:天葬主的大小骷髅、狰狞的护法、汉地以及蒙古服装的将军、寿星,龙王,都旋转着出现,又旋转着消失在大殿内。我时睡时醒,这像是一个漫长荒唐的梦。
经过一夜,漫长的金刚舞终于要结束了。初生的朝阳里,我的藏文老师泽批喇嘛戴着高大的鹿头面具,从寺庙的大经堂里一路跳出来,万众欢呼,它左顾右盼,神采飞扬,谁也不知道这是个经常胃痛,说话都腼腆的结巴的喇嘛,他高高跃起,手指直指半空,莫名其妙传来一声炸响。
寺庙一角准备好的喇嘛们敏捷地倒下火堆上的酥油盆,大火猛地跳到半空。全场汉子乐的哇哇乱叫,这就是新年仪式的最后一章:烧鬼。
男人们从二楼扑通扑通跳进人群里,大呼小叫,“扑日”包子和“拉多”果子统治理塘的藏历年到来了。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疯一样向外挤,二楼屋檐上的人也莫名其妙向下跳,像遭了冰雹一样挤出寺庙的窄门。小伙子们趁机乱挤姑娘,兴高采烈地高叫,老人笑眯眯地遥望。故作矜持,嘴唇鲜红的姑娘们害羞的脸颊绯红,假装生气。一对颀长漂亮的姐妹被挤的最惨,几乎哭出来,她们整齐的头发都挤散了,金耳环直晃悠,被莽撞的半大男孩子吓的心惊胆颤。
山谷里鞭炮声四起,硝烟从所有的窗户和屋顶上漫出来,巨响回荡,杀气腾腾。人潮推挤向庙门外冲,把我藏袍上的铜钮子挤没了,我们已经被挤出了庙门。
藏历年就此开始。
那真是大醉一般的日子。
十家人家,大约总有70多人,聚集在曲西家的大客厅里,牦牛头肉(康巴话语叫松阔)硬如铁石,这条小街上所有的姑娘都来了,盛装打扮,沉重的金耳环,然后依次羞答答起来唱歌。许多人家我不认识,名字也叫不上了,而且许多人名字是一样的。于是我给他们随意起外号:“黑大妈”、“老实人”、“大眼睛”。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我对他们是多么熟悉啊!春天的时候,我曾见他们忙的浑身热气,把糌粑酥油干牛肉,被褥锅碗干牛粪等全副家伙装上拖拉机,男人们绒线帽歪扣在乱发上,女人提着水瓶,紧抿嘴唇。最终,他们爬上堆的高高的拖拉机,摇摇晃晃,挥手告别,前往更高处积雪的牧场去挖虫草。留给理塘一条空空的街道。
夏天的时候,我见到他们在街道上猛烈地吐痰和擤鼻涕声。他们在街头的虫草市场交易,虫草新鲜上市,很有股票市场开市的意思。打着英雄结的焦虑的康巴汉子,带着西部帽的商人,在放虫草的竹篾匾前挤挤挨挨。他们并不会当面讨论价格,而是像祖先一样,在某一方的袖子里或者在虫草匾的掩护下,用手势谈价格。拇指除外,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捏住几根手指就是几,轻轻旋转手指表示乘二,等等妙算,如同手指杂技。
或许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大醉吧。
牦牛肉包子传进来,雾气腾腾,所有人都在雾气中大嚼。
“扑日”包子无所不在,想要逃跑,可以下到院子里跳锅庄,我发现四岁的降措的节奏感都比我好得多,跳得小腿生疼的次仁也退下来,指着他的儿子降措说:“啊呀,以后降措凶得很。”他的意思是说,降措这么会跳舞,长大以后追姑娘简直是得心应手。
好吧,我想这样度过我的藏历年,我在朋友后面,我在亲戚后面,我在陌生人后面,我在无数酒杯和包子的后面。在可供上百人以中世纪方式大吃大喝的酒席上,时刻有歌声,有呼噜声,念经声,还有私密的角落,可以供伤心的人哭泣:人总有些时候会伤心的,有地方哭也是种幸福。
夜是最纯净的醉,星星都是幻觉的点缀,家家扶得醉人归,远处还听见唱歌声。
我和曲西去送几个妯娌回家,我几乎是扛着一个喝醉的巨汉,他康巴汉子的红头缨擦着我的脖子。清冷的北斗星壁虎一样趴在铁虎年第一天的夜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