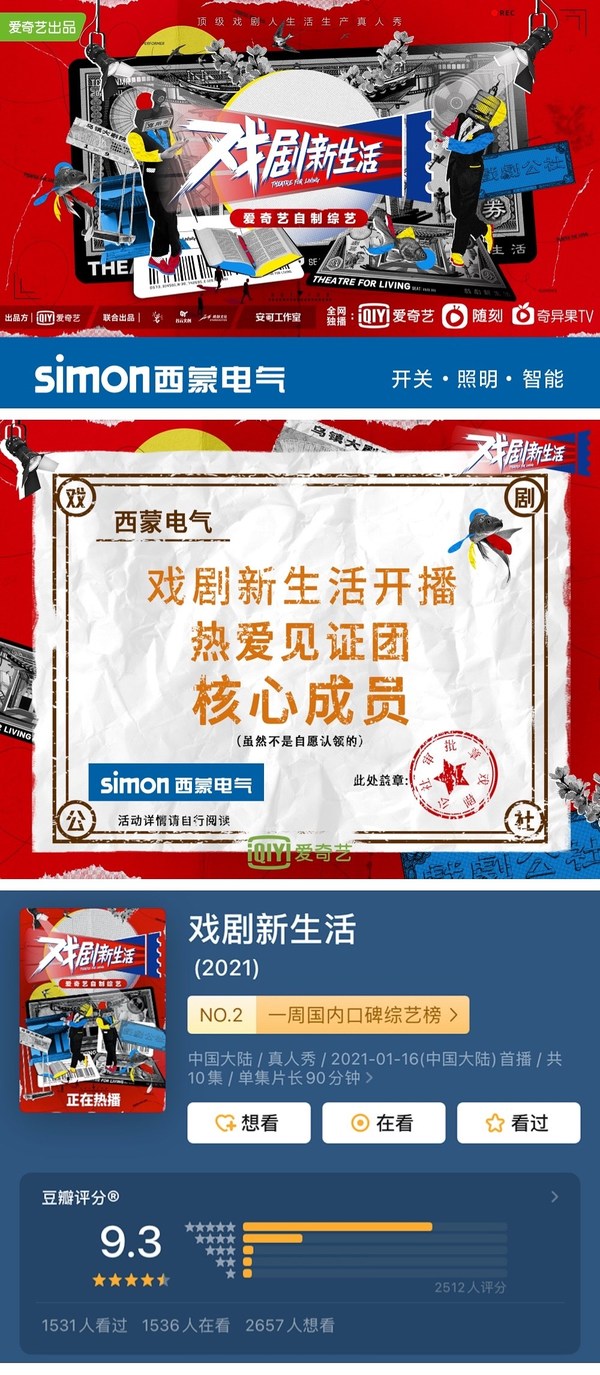文/克努特·奥维·安提兹+译/袁朝云+张欣欣
一、戏剧的新意识:现代主义运动
挪威戏剧和后现代主义戏剧的新剧作方式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这种自由戏剧摒弃了古典主义戏剧作法以及叙事诗结构的替代模式,通过自由结构来表达不同观点,从此意义上讲,戏剧中的后现代主义意指一种全新的模仿或后对白。不过此种戏剧文本仍然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可由戏剧制作呈现出来。而现代主义浓厚的激进主义倾向导致了戏剧结构的解体,但也把戏剧文本提升到与戏剧制作比肩的高度,赋予了戏剧文本独立存在的特权,为戏剧文本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后现代手段。因此,时至今日,任何形式的文本都可以成为戏剧文本。
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为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另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他以梦幻戏剧写作手法和固定的戏剧结构创作了后地狱危机戏剧,以此颠覆了传统,创造了更为开放的戏剧结构,对20世纪初的戏剧影响深远。易卜生和斯特林堡这两位大师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影响了欧洲戏剧,斯特林堡的表现主义在德国备受推崇,而易卜生则影响了乔治·伯纳·萧的创作,后者将其发展为安格鲁-撒克逊的现实主义传统,易卜生也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精髓)的鼻祖之一。易卜生的戏剧仍然采用象征手法,注重层次,含有大量固定对白。但是现代主义运动反对戏剧对白中的模仿因袭与戏剧的分层结构,上至赫赫有名的斯特林堡、魏德金德、格特鲁德·斯坦,下至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卡巴莱艺术家及剧作家朱拉·索夫尔都可以证明。
在世纪之交,再戏剧化和先锋派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其别具一格的特点可追溯至早期的卡巴莱艺术和19世纪90年代的象征主义。在巴黎的黑猫夜总会(卡巴莱夜总会)竣工之后,卡巴莱艺术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欧洲,于1881年至1897年达到鼎盛。
卡巴莱艺术起源于皮影戏,这种视觉艺术将灯光从后方照射在透明幕布上,通过幕布后的剪影来讲述故事,它源于东方,于18世纪传入法国后轰动一时。此后波尔卡酒馆、巴普卡德阿格(B??nkellieders??nger)在中欧方兴未艾,在德国尤为风靡,市集剧院娱乐传统和马戏团也开始流行。在一篇描写马戏团、市集剧院以及卡巴莱艺术的文章中,法国研究者让·劳昂(Jeanne Lorang)阐述了这些发展如何影响了早至魏德金德,晚至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1)的德国现代戏剧家。魏德金德发明了新型戏剧创作方法,这得益于他对皮影戏哑剧剧本的深入研究,而且20世纪风靡法国的大道喜剧也激发了他的灵感。大道喜剧虽然深植于流行歌舞杂耍表演与情景剧,但是文学色彩浓厚,诙谐幽默,象征意义深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金·拉比什就是明证,其部分作品为戏剧性漫画或该时代的动画,既传承了写作传统,又同亨利·维科塔一道预测并引领了荒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戏剧运动的发展。超现实主义戏剧与斯特林堡的梦幻戏剧写作手法颇有渊源,又由梅特林克发展为象征主义戏剧,其戏剧的线性结构不断解体,新剧结构则大量借鉴了卡巴莱与戏剧评论的元素,并逐渐开始取代前者。玛丽安·凯斯廷明确指出,魏德金德添加了面具、舞蹈和其它具有表现主义(2)特征的戏剧元素,使统一剧作法广为接受,为戏剧做出巨大贡献。依我之见,魏德金德引领了视觉化戏剧作法(3)的发展。
克努特·汉姆生的戏剧也带有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也许是易卜生的影响太过深远,汉姆生从未觉得自己的剧作家身份被挪威人认可。虽然他的戏剧很少在舞台上演出,但1988年在瑞士导演弗朗索瓦· 罗卡克斯(Rochaix)的指导下,卑尔根国家剧院推出了他的戏剧《游戏人生》。这部作品极富视觉效果,充满诗意风格,最贴近自然天性,讲述了一位名叫卡雷诺的哲学家退出了奥斯陆大学知识分子们的高雅沙龙,在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上自我放逐,剖析自己内心情感的故事。可以说,汉姆生大大推动了挪威戏剧的现代化进程。挪威戏剧的整个发展历程隐蔽而神秘,对于之后的挪威剧作家如斯坦·布格(Stein Bugge)、塔基·维萨斯(Tarjei Vesaas)与西西莉·鲁维德等而言,戏剧之路崎岖而坎坷。可是纳达尔·格里格是个例外,他努力创作了挪威现代政治,并将固定剧作法成功地运用于其中,因而为布莱希特所深深敬仰。布莱希特在创作关于巴黎公社的剧本时,也从格里格的《失败》中汲取灵感。依我愚见,布莱希特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是否要创立一个新体系,以便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模式进行修改,而不是完全取而代之。或者更直接的说,在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现代主义潮流滚滚而至时,史诗戏剧能否挽回黄昏中的古典主义戏剧?
他们继承了斯特林堡和魏德金德的梦幻戏剧和固定戏剧模式,先锋派运动是否会终结呢?我想,戏剧本身的发展就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由于对再戏剧化和对剧场新环境和新功能的深入研究,现代主义传统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认为,戏剧不仅是文字的呈现,更是舞台上的表演,戏剧指挥和编舞成为了导演,这也就意味着,剧作家已逐渐失去其传统地位,只有人们像对待剧本、视觉效果、舞台空间以及人物的正面描绘那样接受戏剧作法时,剧作家才能获得创作的自主空间。此时的剧作家可以为戏剧制作提供素材而不必完成戏剧作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视觉化剧作法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再循环和后现代主义杂合特征的出现息息相关,表明了演员可利用剧作家提供的素材,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来即兴创作台词和舞蹈动作以进行表演,在时光流转或快慢动作转化间完成独白。这时演员们的许多动作借鉴了如罗莎舞团、法伯(Fabre)和尼德卡玛尼(Needcomany)等八十年代的舞蹈和戏剧,说明早期或近期的戏剧风格元素已经融入新的综合体,其中《告诉世界》可视为模仿前人的巅峰。而“有意识的再循环”必须精心运用一些视觉效果。“你一旦全情投入,就会意识到这是真的。”简单来说,再循环将创作戏剧的自由与一些意图相融合,这些意图包括不同风格的混合、对戏剧的专业研究以及对戏剧和其特性的全新质疑,以此把剧院变成创作独立剧本的实验室。再循环也可能是“空间布置”的问题,或是对昔日戏剧作法的模仿与创新,或是制造幻觉的戏剧把戏。即使像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及维尔纳·施瓦布这样的奥地利当代剧作家与西西莉·鲁维德这样的挪威剧作家,也为这众多的可能性所深深吸引,不能自拔。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后现代戏剧文本的先行者,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旅居巴黎,其作品对美国视觉化戏剧作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罗伯特·威尔森、理查德·福尔曼和伍斯特剧团都从其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她的戏剧注重人物肖像刻画,没有具体的动作描写,不按照一般的戏剧套路创作,也不采用直线式或叙事式结构。20世纪30年代的澳大利亚卡巴莱艺术家、理论家、剧作家朱拉·索夫尔就与格特鲁德·斯坦的写作方式有几分神似,他使用的框架和“非情景式”手法,对分裂与无意义极具讽刺意味。1937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阐述了当时法国戏剧的特殊发展趋势,并将此趋势与一场声势浩大的作家运动相联系,参与此运动的作家们都主张将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融为一体。他评论道:“今日的法国涌动着一股强劲的作家思潮,他们研究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为艺术的永恒做出了巨大贡献。”(4)在我看来,这是对即将到来的荒诞主义的预言,也是深植于流行喜剧与先锋艺术中的文学戏剧的发展方向。索夫尔自己也顺应了这股潮流,他具有浓厚的卡巴莱传统,精通小舞台剧(Kleinkunst),在中欧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这种行文方式,才有了我们时代、混合形式和新模仿主义的循环。因此,在后现代或后对白的情境下,剧作家自己会怎样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将介绍一下作家费恩·昂克,他既是剧作家,又是剧院工作人员(该剧院与挪威卑尔根的挪威戏剧艺术项目相关),他创作的《答录机》非同凡响,引起了国际戏剧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二、戏剧艺术项目:剧作家事业的追随者
通过上文对戏剧发展的大致描述,在出现现代舞台导演之后,剧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冷落。此后,剧作家与剧院的关系开始日益密切,这表明了剧作家正在逐渐认识剧院的种种新机遇,也逐渐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戏剧文本的发展已经赋予剧本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新型戏剧作法相关,而且在新型戏剧作法中不同的表现方式也可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目光投向卑尔根的挪威戏剧计划(此处指挪威戏剧艺术项目)。它于1992年启动,由卑尔根国际剧院协办,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现有条件创作出名副其实的创新型戏剧文本。换句话说:在挪威创作戏剧文本时,如何开辟新的疆土获得新的体验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戏剧的创作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桌前。剧作家或文本作家一定要将自己视为剧院制作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将自己归为戏剧工作者。而体制化的剧院则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它们缺乏主动性,不会运用创新思维去思考创作对剧院真正意味着什么。创新思维意味着排演小型实验剧,转变人们对剧院与剧作法的固有观念,而新型剧院与新型戏剧也在传统戏剧和创新实践的激烈碰撞中诞生了。另外,剧作家的光芒已不复往昔,在重视导演的传统中,他们显得有些无足轻重。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视觉化剧作法的发展,当代以导演为上的剧院传统经历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包括台词的演释以及大量比喻的使用。此时,各种类型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剧本来使用。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效果,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创作剧本。而这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运动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法国太阳剧场的演员们自己搜集素材创作剧本进行表演,赋予了剧本创作以完全的自由,致使传统意义上的剧作家概念逐渐淡化。不过这也开辟了剧本创作的新思路,以此为基础,剧作家/作家和剧院的合作才成为可能。剧作家独立创作的思潮已经涌现,可是创作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剧院环境的观点也已深入人心。这促成了自由写作方法的飞速发展,自由写作方法与格特鲁德·斯坦的静态肖像描述技法有几分神似之处。有趣的是,在1992年的一个春夜,卑尔根市举行了一次会议,首个挪威戏剧艺术项目正以“格特鲁德·斯坦沙龙”的形式拉开了帷幕,其中因格利·楼尼伯与玛丽安·索尔伯格担任此项目的导演。会上展出了格特鲁德·斯坦的作品节选拼接版及参加者的评论词。
西西莉·鲁维德是挪威当代戏剧创作的先驱。她的戏剧Balansedame(Balancing Lady)于1985年在卑尔根国家剧院上演,该剧舞台布置极具透视感,剧中有大量独白及关于存在主义的描写,让人联想起现代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和海纳·米勒的作品。但是体制化的剧院通常不向这样的实验型戏剧敞开大门,所以像巴克·特鲁本剧团和世界剧院这样的新型剧团才填补了当时的空缺。世界剧院才有幸与西西莉·鲁维德合作,于1989年在奥斯陆的阿科瑟尔瓦(Akerselva)河畔上演了她的戏剧 《浴室》。可以说,巴克·特鲁本剧团和世界剧院以及像凯·约翰森和谢蒂尔(Kjetil Skoien)这样的年轻导演为挪威戏剧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1993年评论家汉斯·罗瑟尼(Hans Rossine)在文章中认为当代剧院正在向新型戏剧表达和新型假设的程式化的方向发展(5),这可以解释为戏剧对专业环境的需要,专业的环境正如19世纪50年代易卜生在卑尔根的工作环境一样,有剧作家、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还特别需要一名优秀的艺术总监。极为有趣的是,从极具主动精神的挪威戏剧艺术项目上就可窥见一些“卑尔根传统”。此外,卑尔根国家场景剧院的导演汤姆·瑞楼伍(Tom Remlov)起步很早,他启动了另一种形式的戏剧项目,鼓舞了像阿凌·格斯伍克(Erling Gjelsvik)、 贡纳尔·士塔勒森(Gunnar Staalesen)和乔恩·福斯等知名挪威作家将其作品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这也与霍达兰写作学院(以下简称写作学院)密切相关,它在1985至1987年间开设了第一门课程,汤姆·瑞楼伍(Tom Remlov)和西西莉·鲁维德曾是当时的主要教师。根据创作戏剧文本的自主性原则,自1991年起,编剧课程就更多地向后现代写作风格靠拢。1996年挪威评论家、广播编辑卡尔·亨利克·格朗达尔就在其出版的书中描写了汤姆·瑞楼伍在卑尔根担任剧院导演时的经历。(6)
从1991年至1994年,写作学院的课程大纲以项目为导向,来自巴克·特鲁本剧团的托尼·阿文斯托普(Tone Avenstroup)与凯·约翰森担任导师,他们要求学生们必须跟进自己的作品,参与制作过程并有所贡献,从而在戏剧工作中追求更深程度的一体化。所以作家若想成为戏剧家,就必须融入戏剧的制作过程,而不是仅仅作为自己戏剧的观众或者“顾问”,这是前提。虽然当时戏剧制作的周期短,可利用的资源也非常匮乏,但是这种思想发展成了Canapé这一全新的戏剧类型。费恩·昂克在1991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当时他还在学习戏剧课程。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小型戏剧易于演出,可与展览会或者其它形式的文化事件相结合。人们应该以理解寓言的方式来看待Canapé,在标准戏剧的形式中,将同样的对白视为历史的前奏、插曲和收场白。Canapé与表演艺术也息息相关,可视为一种杂技剧院或零点剧院(7)。它虽然形式短小精悍,但却极其适用于抽象文本、形象片段、情景或描述文本的实验性研究,在表演过程中不需要矫揉造作,但却要求技术上的准确无误。这种戏剧的参与者或演员不拘出处,背景各异,可来自项目剧院、体制化的剧院,也可以是舞者。最有趣的是,1992年10月,在古老的挪威银行大厦里,来自卑尔根国家场景剧院的拉根黑德·海澳(Ragnhild Hiorthoy)和黑尔格·乔达奥与来自巴克·特鲁本剧团的英格维尔特·霍尔姆联袂出演,将茵格·楼尼伯(Ingri Lonnebotn)的剧本《森林》搬上舞台。零点剧院的重要特点是戏剧制作条件简陋,预算极其紧张,而这也是挪威戏剧艺术项目的运作方式。
三、剧作家与戏剧工作者的合体:费恩·昂克的自主创作之路
如上所述,费恩·昂克于1991年秋季参加了写作学院的戏剧课程。而在此之前他认为,尽管戏剧对白与电影对白都试图使用自发的语言来创造一种假象,一种幻觉,但是电影显得更加真实。这也就使得昂克“更加相信电影对白,而对戏剧对白嗤之以鼻”。换言之,电影对白比戏剧对白更适合作为传达信息的媒介。“因此,我一直对戏剧不怎么感兴趣,直到参加了写作学院的戏剧课程后才有所改观。在学习初期,我观看了比利时罗莎舞团的表演,深感震撼,这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8)他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戏剧课程中的戏剧表演与舞蹈表演,也从去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远足中收获颇丰,在那里来自比利时和丹麦的重要作品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戏剧课程的最后部分是戏剧制作,对他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正因为参加了戏剧的制作过程,才了解到戏剧的严肃性,明白了若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就必须参与剧院工作。“因为必须参与自己剧本的制作,我有点像戏剧工作人员了,对戏剧的热情也激发出来了,我能感觉到将来种种的可能,渴望多看看挪威和国外的表演以及自己的剧本,靠一己之力继续研究下去。”(9)结课后,他与同事玛丽安·索尔伯格一道向剧院提出不应该把重心全部放在剧本上,剧本只是戏剧制作过程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戏剧。在罗莎舞团客串演出《斯塔拉》(Stella)之后,他与玛丽安·索尔伯格考虑将剧本呈现给观众而不是将其付梓,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文本,也不是为了出版发行才进行创作的。但此项计划最终流产了,昂克认为剧作家应该遵从传统剧院和体制化剧院相关的惯例,或者说应该遵循挪威社会风气中的“易卜生传统”,我们姑且把这看成杀害传统“宠儿”的凶手吧。
昂克曾在1991年12月与玛丽安·索尔伯格一道向卑尔根国际剧院的斯文·老伯可兰德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这些见解得到了积极回应,他的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促成了挪威戏剧艺术项目的诞生。1992年的1月法国剧团Theater du Radeau客串演出《羊之歌》(Chant du bouc)时,他们的Canapé处女作就以小型开场戏的形式与公众见面,虽然在首演时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和问题,但一开场就获得连连褒奖,需求不断,一发而不可收,这使昂克更加确定Canapé会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春,他参加了几场演出的制作过程,并与玛丽安·索尔伯格一起为演出创作剧本,例如1992年5月古老挪威银行布景展览开幕式上的小型Canapé就出自昂克之手。戏剧艺术项目的演出大受欢迎,到秋天时热度也丝毫不减,这让昂克的剧本写作经历也日益丰富。他曾与来自巴克·特鲁本剧团的伯·克里斯特·沃斯特姆(Bo Krister Wallstrom)携手打造一场演出来描述帕斯卡,该剧历时四十分钟,以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文稿为蓝本,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次合作让我收获颇丰,我学会了把不同素材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布莱斯·帕斯卡的和我自己的,也让我明白了在戏剧制作过程中,不能只对别人的文本吹毛求疵,对自己的也应该无情一些。”(10)并且他明白了从戏剧制作之初到表演之刻,蕴含新内涵的场景会不断涌现。在1992年的戏剧艺术项目中,舞台设计师奥拉乌·迈特伍德(Olav Myrtvedt)与来自巴克·特鲁本剧团的托尼·阿文斯托普(Tone Avenstroup)和汉斯·皮特·达尔(Hans Petter Dahl)联袂打造了三场演出并在国家剧院的小型舞台上演,至此,当年的挪威戏剧艺术项目完美闭幕。从1993年到1995年,这种合作形式在挪威戏剧艺术项目中分三个阶段持续进行,并且这个项目得到了挪威艺术委员会的慷慨资助,志同道合之人也纷纷加入,例如赫赫有名又深谙戏剧艺术的挪威作家瑞格纳·侯伍兰德(Ragnar Hovland)和伊万德·伯格(yvind Berg)就位列其中。1993年的挪威艺术项目在昂克的作品 《每手一笔》(Med en blyant i hver hand)中落下帷幕(其中凯·约翰森任导演,国家剧院的14名演员参演)。“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趣,训练有素的演员们摆脱了原有的演出题材,进行了新的尝试。此剧本由一系列描述性的句子构成,每个句子都有各自的角度,包含了一些片段和简短的独白。在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课程学习中,我先是创作一些剧本片段,然后是一个长一些的剧本,这也让我在创作更大型的剧本时游刃有余。1993年10月,我联系了阿姆斯特丹市的达撒茨(Dasarts)学院,欲拜瑞特撒克特·特恩·凯特(Ritsacrt ten Cate)为师学习戏剧。我向学校电传了个人信息和自己的剧本,但事与愿违,阿姆斯特丹方无法理解挪威语的剧本,这让我觉得一切创作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无力将自己的剧本翻译成英语。无奈之下我只得递交了个人信息,想方设法让他们想到我是谁。”(1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后费恩·昂克开始用英语写作,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他的作品也由美国导演约翰·耶书仑搬上舞台,在德国黑森州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上演。1994年7月昂克返回卑尔根,把剧本交给了卑尔根国家剧院,之后又交给了比利时昂特伍普(Antwerp)的STAN公司。他的作品《答录机》于1994年12月在比利时首演,1995年11月在非正式欧洲戏剧会议节中上演,之后又在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巡回演出,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昂克也因此享誉国际。《答录机》(用于剧院演出)的结构简洁紧凑,堪比米勒的《记忆的爆发》(Bildbeschreibung),故事的主人公环游欧洲,主要是在德国,他在途中倾听了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经历,同时也体验了完整的人生。昂克创造了一种新的剧本,此类剧本不同于传统的对白,可以自由地运用特殊的独角戏形式,从而解放了开放性戏剧的舞台潜能。当昂克意识到《答录机》既可以作为独角戏来演,又可以由几个演员共同表演时,十分惊奇。(12)
1996年,《答录机》被译为法语,三位演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戏剧研讨会Les 20 Jours du Theatre a Risque(20 Days of Risky Theatre ,危险剧院20天)上将其演绎出来。此时,费恩·昂克已经返回阿姆斯特丹的达撒茨学院继续工作。最后我想说,他清晰地表明了剧作家蜕变为戏剧工作者的成长历程,我将之毫不隐讳地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对戏剧文本的解读过程。
注释:
(1)Lorang, J., “Cirgque, champs de foire, cabart ou de Wedekind à Brecht ”,Thé?tre Annees vingt: Du cirque au Thé?tre, ed. C Amiard-Chevrel, Lausanne 1983.
(2)Kesting, M, Das epische Theater. Zur Struktur des modernen Dramas, Stuttgart 1972, S.40
(3)Arntzen, K.O., “A Visual Kind of Dramaturgy: Project Theatre in Scandinavia ”,Small is Beautiful, Theatre Studies Publications, ed. C. Schumacher and D. Fogg, Glasgow 1991.
(4)Soyfer, J., Wiener Tag, Vienna, 21.2. 1937. (Translation: Knut Ove Arntzen)
(5)Rossiné, H., commentary article, Dagbladet, Oslo, 4.5. 1993.
(6)Grondahl, C.H., Avmaktens dramatikk. Bergensprosjektet p? Den Nationale Scene 1986-1996, Oslo 1996.
(7)Arntzen, K.O., “Zeropoint theatre”, Active Pooling New Theatres Word Perfect, Amsterdam, August 25-29, 1993, following definition by entry: “Zeropoint theatre, in which starting a production work means dealing with materials as bricks to be totally reused or recycled, something which can also be told as starting from scratch or reinventing meaning. A story is to be told from another story, or like Gertrude Stein has put it: ‘A rose is as rose is a rose. No technical perfection is required, excerpt for technical consciousness as a mean to keep the attention from the audience. Playing with space and playing with the story to be told is essential to Zeropoint theatre, and it can take place anywhere like as street performance or like action in a foyer”.
(8)Iunker, F., in an interview with K.O. Arntzen, Arhus, 10.4.1995,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Diane Oatley.
(9)Ibid.
(10)Ibid.
(11)Ibid.
(12)See also F. Iunker in an interview with K. Seltun, in 3t, periodical for theory and theatre, Bergen, nr. 1-1996.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天津公示语翻译语料库建设》资助,项目编号:TJWY12-043。
作者简介:克努特·奥维·安提兹,挪威卑尔根大学戏剧系教授;袁朝云、张欣欣,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